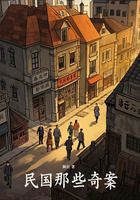
第1章 杨三姐告状案
杨二姐的不幸婚姻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句,几乎成了那个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的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在那个腐朽的旧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行政与司法大权,都握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有人因为身后有权力撑腰,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却依旧可以逍遥法外,无人追究。而那些普通百姓,连一口气的喘息之地都没有,纵使他们遭遇百般凌辱和伤害,也只能默默忍受,冤屈无处伸,只能打掉门牙,忍着血往肚里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常态,没人能反抗,没人能改变。
可这不代表一切,偶尔,总有一些例外。民国初年,便有这样一位女子,她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了旧社会的沉默与压迫,为亲人洗雪了沉冤。她就是年仅十六岁的杨三姐,为了替被人无端杀害的姐姐报仇,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告状之路,与有钱有势的杀人犯对簿公堂。
杨三姐的告状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前后历时一年半,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她被无数次威胁、陷害,甚至在途中遭遇重重阻碍,但她从未低头,始终坚定不移,凭着一股子倔强,与那个既有权又有势的凶手斗智斗勇。最终,她让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姐姐报了仇,替家人洗清了冤屈。
此案发生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评剧作家成兆才听闻此事后,迅速将它搬上了艺术的舞台。《杨三姐告状》这一剧目在数十年间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目,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了无数观众,令人为之动容。
然而,艺术虽源于现实,却并非现实的全貌。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终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那么,关于“杨三姐告状”一案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这得从清朝末年开始说起。那时,在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的主人杨玉清,是个待人和气、憨厚朴实的庄稼汉,整日里辛勤劳作,只为能让一家老小过上温饱的生活。杨三姐是他的小女儿,学名杨国华,聪慧伶俐,深得父亲疼爱。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艰难,贫困如影随形,农田不多,收成微薄,家里实在是捉襟见肘。为了维持家计,杨玉清不得不带着儿子杨国恩到邻近的乐亭去打短工,弹棉花挣点微薄的工钱,勉强度日。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玉清按照传统习俗给自己的三个女儿都找了“娃娃亲”。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金家的儿子,二女儿则许配给了高家狗庄的高占英。这两个地方与杨家相距不远,几十里路程而已。
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个小贩,与杨玉清只能算是不相上下,双方对这门亲事都颇为满意。
但高贵章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他虽家境平平,却是个精于算计、善于经营的人。几年小贩生涯,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便将目光投向了瓷器这一行。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市场潜力,高贵章凭借积蓄开了一家瓷器店。生意越做越红火,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当地的小有名气的暴发户。
富贵之后,高家也今非昔比,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高占英被送入滦县传习所读书,毕业后回村教书,俨然成了当地的小士绅。
高贵章家在村里办了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院里的厢房。十几个邻村的孩子每天在这里听高占英讲四书五经。高占英本就自诩读过几年书,教书时更是趾高气扬,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
转眼间,儿女们都长成了大人。杨玉清和高贵章按照早年订下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操办了婚事。高家如今已是富甲一方,婚礼自然办得风光体面,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凑热闹,夸杨二姐“真有福气”。杨二姐脸上挂着笑,心里也暗暗盼着婚后能过上舒心日子。
但婚后的生活却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高占英对她的态度冷淡得像是陌生人,动不动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没多久,夫妻俩的关系便跌入冰窖,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杨二姐起初还纳闷,直到从高占英嘴里听出端倪——他嫌弃杨家家境贫寒,觉得杨二姐配不上自己。
这桩婚事是早年两家定下的,高占英虽心不甘情不愿,却也不好轻易毁约。可他却解不开这心结,反而越结越紧。在他眼里,杨二姐就是个累赘,心里那股憋闷无处发泄,便常常对妻子大打出手。
杨二姐心里苦,却不敢声张。每次回娘家,她只报喜不报忧,生怕父母担心。只有杨三姐看出了姐姐的异样。她曾劝父母去高家看看,可老两口觉得女儿已经出嫁,不便过多插手。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忍让竟会断送了女儿的性命。
事实上,高占英早就与五嫂金玉勾搭成奸,觉得杨二姐碍眼。加上金玉挑唆,他渐渐起了杀心。某天夜里,杨二姐亲眼看见高占英偷偷磨刀,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跑到公公那儿求救:“阿公,占英想杀我!”高贵章却不以为然,只摆了摆手:“他不敢,你安心睡去吧。”杨二姐无奈,只能含泪回房。
然而,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在夜里暴毙。次日一早,高家派人赶到甸子村报丧,说是杨二姐得了“血崩”,不治身亡。当时,杨玉清和儿子杨国恩在外打短工,家中只剩下杨二姐的母亲和杨三姐。母女俩听到噩耗,如遭雷击,悲痛欲绝。
杨三姐陪着母亲去高家吊孝。她虽只有十六七岁,却是个心思细腻的姑娘。当母亲扑在姐姐尸身上痛哭时,杨三姐突然注意到二姐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血迹,右手的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她心里顿时起了疑:二姐若真是患了“血崩”,嘴里怎会有血,手上怎会有伤?何况,高占英与二姐平日里争吵不断,二姐回娘家时也曾向自己诉苦。这一切,不禁让杨三姐对高家的说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平冤屈誓不罢休
杨三姐虽满心狐疑,可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敢妄下定论。她极力反对高家草草将二姐入棺下葬,甚至不顾一切上前阻拦,却被高家人生生推开。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尸身被匆匆下葬,杨三姐心如刀绞,只能暗暗咬牙,将这份不甘和悲愤咽下。
几天后,甸子村举办庙会,四邻八乡的乡亲们都赶来看热闹。杨三姐在人群中遇到了几位从高家狗庄来的乡亲。几人闲聊时,又谈起了杨二姐的突然死亡,他们压低声音告诉杨三姐:“你姐死得蹊跷!那天夜里,有人听见高家院子里传出了哭闹声,折腾了好一阵子。”
这番话让杨三姐心里的疑团愈发深重。她几乎可以肯定,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得那么简单。回到家,她将乡亲们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家人,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随父亲回到家中。听完妹妹的叙述,他深感有理,兄妹俩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为二姐讨回公道。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二姐被害十天后,杨三姐骑着毛驴,揣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踏上了去滦县县衙的路。一路上,杨三姐心中既紧张又忐忑,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做得是对的,无论结果如何,她都必须为姐姐讨回公道。
到达县衙时,杨三姐被带到大堂。审理这起案件的是滦县的帮审——牛成。牛成的名声在当地并不算好,许多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自从坐上帮审的位置后,他也常常被传出许多勾结营私的事。牛成此时坐在堂上,摆出一副官威十足的模样,接过杨三姐兄妹递上来的状纸。看了一眼,随便翻了几页,又叫杨三姐说出案件的缘由。
杨三姐口齿清晰,句句铿锵,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怀疑,并举出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说法为证,她的说法显得有理有据。牛成听完,皱了皱眉,随即决定传唤高占英前来应对。
不一会儿,高占英被带到堂前,面对杨三姐的质疑,他一口咬定,杨二姐确实死于“血崩”,对杨三姐的指控矢口否认。大堂之上,杨三姐与高占英针锋相对,互相辩驳,高占英说杨三姐的推测“毫无根据”,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哭闹声”,都不过是无稽之谈。
牛成见状,只得宣布休庭,决定等进一步调查后再审。
几天后,牛成再次开堂审理此案。可这一次,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竟处处为高占英开脱。他对杨三姐的说辞充耳不闻,甚至斥责道:“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无端猜疑,杨二姐死于‘血崩’,这是有证人证明的。”说罢,他传上了一名证人。
杨三姐扭头一看,来人竟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高家狗庄的村医。高作庆一脸笃定,声称“我亲自给杨二姐诊治过病,她的死因确实是‘血崩’。”
杨三姐心中一紧,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关系密切,他的话未必可信。
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请求。此言一出,高占英和高作庆顿时脸色大变,不约而同地望向牛成。牛成略一迟疑,便冷冷地拒绝了,“现在人证齐全,事实也很清楚,不需要再进行开棺验尸。”
杨三姐和杨国恩看在眼里,心中怒火熊熊。他们断定,牛成态度突变,必定是高家暗中行贿,包庇高占英。
事情的真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为复杂。
杨二姐的死,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她的性命,是被高占英亲手害死的。高占英嫌弃杨二姐家境贫寒,觉得自己一个财主家的少爷,娶了她简直是耻辱,早已心生厌弃。而更深的原因,则藏在他与五嫂金玉那段见不得人的奸情里。
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因父亲安排去了唐山瓷器店当掌柜,常年不在家,寂寞难耐之下,从唐山一家妓院买了个叫金玉的女人做小老婆。金玉生性放荡,没有缠足的她在高家如鱼得水,不久便与高占英勾搭在一起。高占英本就嫌弃杨二姐,如今又与金玉有了奸情,越发觉得眼前这个妻子碍眼,心中渐渐起了杀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高占英自以为杀人灭迹,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杨三姐一眼识破了他的阴谋,还直接将案子告上了县衙。高占英慌了手脚,私下贿赂了牛成几千块大洋,求他为自己开脱。牛成拿了钱,自然要替高占英“消灾”,这才在大堂上公然偏袒他。
可杨家兄妹并非轻易放弃之人。他们虽看穿了牛成的贪赃枉法,却依旧坚持告状,誓要为杨二姐讨回公道。高占英见杨家兄妹不肯罢休,便多次托人上门说和,提出用二十亩地和一头牛作为赔偿,想以此息事宁人。但杨三姐和杨国恩毫不让步,将来劝和的人一一拒之门外。
高占英的这些举动,非但没有让杨家兄妹松口,反而让他们更加坚信杨二姐的死另有隐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高占英心里有鬼,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的那么简单。尽管牛成一再拒绝开棺验尸的请求,但杨家兄妹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决定继续上告。
杨三姐和杨国恩的勇敢举动,赢得了众多乡亲的支持。门庄村的杨姓族人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出一块大洋,资助杨家申冤。在滦县告状无果后,杨家兄妹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检察院人员看过状纸,迅速判定此案有冤情,接受了他们的开棺验尸请求,并决定由院长亲自指挥。
真相水落石出
中国人的传统讲究“入土为安”,开棺验尸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高家狗庄周边的客店都被住满,甚至有不少人提前两三天就赶到现场,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幕。
验尸当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仿佛在为杨二姐的不幸哭泣。为了维持秩序,官方在坟地旁搭起了凉棚,旁边还有一锅煮沸的酒精,用于消毒。围观的人太多,挤得水泄不通,喧哗声越来越大,直到现场的法警不得不用马鞭将前面的人群驱赶开。
终于,杨二姐的墓被掘开,棺材盖被打开,现场一片肃穆。随着一声轻响,负责验尸的人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尸体。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在杨二姐的阴部,竟然被插入了一把尖刀。更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杨二姐的裤内,居然塞满了白灰,显然是高占英用来止血的。有知情人回忆,杨二姐被害那晚,确实有人看见高占英在磨刀。杨二姐也曾向公公高贵章哭诉,说自己预感要被杀害。可高贵章只是敷衍一句:“他不敢,你安心睡吧!”结果,当晚便发生了悲剧。
至此,杨二姐的死因真相大白。高占英的狡辩再也无济于事。
然而,事情并未因真相大白而画上句号。在那个时代,一桩案子想要得到公正的判决,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杨三姐和杨国恩心中依旧忐忑,他们深知高家财大势大,生怕高占英能够凭借金钱再次逃脱法网。于是,开棺验尸后,兄妹二人再次踏上了去天津的路,决心紧跟案子,直到亲眼看到高占英伏法为止。
杨国恩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语气里仍带着几分辛酸:“验尸后,我们兄妹俩又追到天津,生怕高家用钱财打通关系,把人放了。为了糊口,我只好去洋人开的牛奶厂做苦工,一个月挣四块洋钱。那段时间,我们在天津过了个年,连家都没敢回。几个月后,终于听说高占英被处死了,据说是绞刑。等我赶到刑场,人早就散了,现场只剩下一些闲谈的百姓。”
1919年10月6日,天津的《益世报》刊登了一则短讯:“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这条简短的消息,对杨家兄妹来说,却是一年多苦等的结果。为了这一天,他们甘愿在异乡受苦受累,连春节都不敢回家。如今,案子终于有了结果,兄妹二人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既为姐姐的冤屈得报而激动,也为这一路的辛酸而悲伤。
案子告一段落后,杨国华嫁到了本县双柳树村一户姓薛的富裕人家。这家人虽是庄户小财主,但性格软弱,娶杨国华进门,是为了让她“顶门户”。杨国华婚后生育了三子二女。她出身贫寒,深知穷苦人的艰难,因而总是心怀善意。据曾在薛家打过长工的人回忆,杨国华心地善良,经常为长工缝洗衣物,嘘寒问暖,还不时接济他们的家庭,深受人们的敬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听说了杨国华的事迹,特意带着刺刀去试探她,想看看这个名闻乡里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胆量。面对侵略者的恫吓,杨国华面不改色,毫不畏惧,俨然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解放战争初期,她还利用自己的名声和经济条件,保释并营救过多名我方村干部,为革命事业尽了一份力。
新中国成立后,杨国华被定为富农分子。在“文革”期间,她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才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她应有的关怀和照顾。晚年的杨国华担任了唐山市政协委员和滦南县政协委员,继续为地方事务贡献力量。1982年春天,滦南县的领导探望了她,表达了对这位曾经的讼案英雄的敬意。1984年1月7日,杨国华病逝,享年83岁。
在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评剧创始人之一成兆才将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搬上了舞台,创作了经典剧目《杨三姐告状》。剧本初稿有70余场,涉及100多个人物,虽然后来经过多次修改,但始终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情节,成为评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