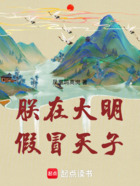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59章 京营主将人选问题
张祁一时间竟对石亨生出了几分同病相怜之感。
北京保卫战之前,石亨的工作环境可太令人窒息了。
同一个衙门里,只有石亨他这么一个没背景的牛马是真正干活的,其余同僚,不是来镀金的勋贵子弟,就是能随时给皇帝打小报告的亲信太监。
石亨不仅得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还得曲意逢迎,给那些勋贵子弟提供情绪价值。
同时还要应付给自己穿小鞋的监军太监,得时刻提防这些奴才的明枪暗箭,必要时还得拉下脸面豁出去跟这些狗腿子撕逼扯头花。
在这样恶劣的职场环境中,石亨竟能步步高升。
单凭这一点,就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张祁心中五味杂陈,因为他穿越前也是个普通人,石亨那种怀才不遇的憋屈,处处受制的愤懑,他都懂。
可正因如此,他更想不通石亨在“夺门之变”中的选择。
换作是他,遇到于谦这样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将自己从边关苦寒之地提拔出来,更给了建功立业的机遇,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
至少绝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张祁暗自踌躇着,他本想趁势进言,劝孙太后撤换石亨,将北京保卫战的统帅之位转予杨洪。
可转念一想,于谦既已如此力荐石亨,自己若贸然反对,岂非当众折了他的面子?
他不由想起前番欲借清除王振余党之机牵连王骥时,于谦那番义正辞严的驳斥。
眼下石亨确实无可指摘,更无实证能料定其日后必会背主求荣,这般无端猜疑,若说出口来,反倒显得自己心胸狭隘。
更何况,孙太后若对石亨心存芥蒂,那对杨洪只怕更为嫌恶。
毕竟石亨虽在阳和口兵败被贬,但杨洪可是当真将皇帝拒之于国门之外啊。
这般“大逆不道”之举,在孙太后心中怕是比石亨的败绩更不可饶恕。
张祁心中几番权衡,终是决定暂且给石亨一个机会。
他暗自盘算道,石亨与于谦反目成仇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待北京保卫战功成之后,尚有八年光景可以徐徐图之。
若能以恩义相结,以利害相诱,未必不能将这员虎将收为己用。
倘若实在难以驯服,届时再寻个由头除去也不迟。
孙太后何等精明,自是也听出了石亨的真实水平,她神色稍霁,将前番怒意收敛了几分,“如此说来,阳和口之败倒真是情有可原,郭敬这奴婢处处掣肘,任是孙武再世也难展拳脚。”
于谦立即应道,“殿下明鉴万里。”
孙太后沉吟片刻,道,“既然石亨已调回京师,郭敬这等王振余孽也该有个了断,总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
张祁心头猛然一颤,后脊倏地窜上一股寒意。
郭敬固然恶贯满盈,论罪当诛,可终究是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帝王的老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如今孙太后要处置郭敬,哪里是真在乎什么王振余党?
分明是要拿这奴婢的性命,给石亨做顺水人情,好教石亨念着天恩浩荡,以为是皇帝为他铲除了政敌,要这位边关悍将对天子感恩戴德。
思及此处,张祁只觉得齿冷,郭敬这个为老朱家卖命了大半辈子的老奴,到头来不过成了孙太后笼络将心的筹码,轻飘飘得就被舍了出去。
于谦神色如常,依礼叩首谢恩,对孙太后的处置毫无异议。
孙太后又追问道,“石亨戍边多年,受郭敬压制,你调他回京将功补过,老身准了,可那焦敬与赵荣二人,你又作何解释?”
于谦从容奏道,“焦敬乃是仁宗皇帝第二女庆都公主之驸马,而赵荣系赵彝之子,这赵彝在洪武年间任永平卫指挥佥事,靖难之役时归顺太宗皇帝……”
孙太后不耐烦地打断道,“老身要问的不是这些陈年旧事!先说这焦敬,他名义上是皇帝的姑父不假,可正统五年时,庆都公主就已薨逝,人都走了这些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夫妻情分可言?”
“再说正统八年时,六科十三道联名弹劾焦敬收受留守卫舍人贿赂,更纵容其在外私征债务,闹得民怨沸腾,最后皇帝命人将他枷在长安右门示众,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于谦回道,“臣当时仍在河南、山西巡抚任上……”
孙太后冷笑一声,鎏金护甲重重叩在案几上,“休要拿外放任职来搪塞老身!你于谦的同年故旧遍布朝中,这等轰动京师的大事,你又岂会不知?”
“那长安右门是何等去处?百官上朝必经之地,每年‘秋审’、‘朝审’的刑场门户!在这等要地枷号示众,除非是个睁眼瞎,否则谁能看不见?!”
这一点却不是孙太后夸张。
按照大明的规章制度,每年阴历八月中旬,皇帝将派刑部堂官会同各大臣,在西千步廊举行“秋审”。
由东到西,几十张八仙桌红毯铺就,判官北面而坐,将各省死囚案牍逐一勘验,互审各犯判文,待诸官批示后,案卷即呈御前,天子朱笔勾决,便是生死立判。
至于“朝审”,则更是令人胆寒,五城兵马司差役自刑部大牢提出秋审定谳的死囚,押至长安右门外列队。
众囚犯须自南门洞鱼贯而入,于公案前三尺外跪成横列,听候审问。
依制,囚徒不得申辩喊冤,只能静候发落,待冬至拂晓,囚车便载着这些死囚奔赴西市刑场。
每当犯人由长安右门提解入内,则犹如身进虎口,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故而长安右门又被称之为“虎门”。
张祁听罢,不由得对明英宗有了一点儿改观,将自己姑父枷号示众于长安右门,此等惩处虽不及下狱问罪来得严厉,却胜在震慑朝野。
堂堂驸马竟因收受贿赂、私放高利贷而被当众羞辱,这等新鲜事怕是顷刻间就传遍了京城内外。
何况庆都公主虽已薨逝多年,焦敬终究还是正经的皇亲国戚。
明英宗能不顾宗亲情面,这般严惩贪腐,倒也算是为黎民百姓狠狠出了口恶气。
孙太后却丝毫不觉得此事彰显了天子的刚正不阿,反而哽咽道,“那几十斤的沉枷往脖颈上一套,数九寒天跪在长安右门外,日日受百官指指点点,一枷枷上一两个月,这般奇耻大辱,换作是你,你能不怀恨在心?”
“经过那么一遭儿,你竟还让这焦敬执掌神机营,你安的是什么心?倘或也先挟持皇帝兵临城下时,焦敬因记恨前仇,暗中命底下人放冷枪,一枪打死了皇帝,那该如何是好?”
张祁心想,此事若放在现代社会,正常人被这么一枷,遭受这般当众羞辱,必定会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但根据目前他的所见所闻,在这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人均受虐狂。
于谦的受虐倾向格外严重,莫说是枷号示众,历史上的明英宗就是当真要了他的性命,他也只会叩谢天恩,哪里敢有半点怨怼之心?
果然,于谦闻言当即俯首叩拜道,“君父责罚,岂敢存怨?臣记得,正统十年时,六科十三道曾弹劾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位公侯、驸马、伯、都督懒慢不朝,请旨治罪。”
“陛下有言,大臣者,小臣之表率,遂命徐显宗等人罚跪午门示众,魏国公乃中山王徐达之后,世受国恩,尚且因怠慢朝仪而受此惩处。”
“可见陛下执法,不分亲疏贵贱,勋戚犯法,亦是一视同仁,焦敬之事,实非特例。”
孙太后冷冷道,“中山王他们家可不一样,他家是一门两国公,你单拿魏国公这一支说事儿,岂非避重就轻?倘或你觉得这惩处无足轻重,不如你现在就去戴枷跪午门,亲自尝尝这滋味如何?”
中山王徐达是举世公认的大明第一开国功臣,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便将徐达封为了开国六公爵之首的魏国公。
徐达去世后,更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其长子徐辉祖顺理成章地承袭了魏国公的爵位。
照理说,魏国公这一脉本该世袭罔替,永享尊荣,然而靖难之役的爆发,却让徐家陷入了两难抉择。
时任魏国公的徐辉祖坚决站在了建文帝的这一方,甚至亲自率军抵御燕王大军。
待明成祖攻破南京,徐辉祖仍不肯俯首称臣,明成祖震怒,命法司严刑逼供。
谁料徐辉祖提笔便写下明太祖赐予徐达的丹书铁券内容,“中山王开国功臣子孙免死。”
明成祖碍于其是元勋之后,加之又是自己的小舅子,最终只得削去其爵位,勒令归第思过。
而徐达幼子徐增寿却在靖难期间暗中襄助燕军,屡屡将建文帝的军事部署密报给明成祖。
南京城破前夕,建文帝察觉其叛行,当面质问时,徐增寿竟默然不语,建文帝盛怒之下,亲手挥剑将其斩杀于殿前。
明成祖登基后,感念徐增寿的从龙之功,特追封其为定国公,并恩准世袭罔替,其后永乐迁都时,定国公一脉举家北迁,定居京师。
至永乐三年,徐辉祖病逝,明成祖以“中山王不可无后”为由,特旨准予徐辉祖长子徐钦承袭魏国公爵位,仍居南京旧邸。
至此,徐达一门出了一王两国公,子孙分袭魏国公、定国公双爵,一脉镇守南京,一脉拱卫北京,两脉并立,同享国公尊荣,直到明朝灭亡。
因此,魏国公徐显宗这一脉,本就是当年在南京拥戴建文帝的徐辉祖后人,自然比不上在北京追随明成祖的定国公一脉得圣心眷顾。
明英宗以“偷懒不上朝”这种小罪罚其跪于午门示众,与其说是苛待勋贵,不如说是略施薄惩罢了。
于谦长叹一声,道,“殿下,焦敬在正统八年受罚时,已非初犯,早在正统元年,他便指使司副于文明门外五里开设广鲸店,网罗市井无赖,假借牙行之名横征暴敛,累计敛财数十千钱。”
“其爪牙还在武清县马驹桥拦截商队,强扣瓷器、鱼枣等货物,又在张家湾、溧阳闸河等商路要冲,诈收米粮八九十石,折钞上千贯。”
“按照《大明律》,受财枉法,赃满八十贯当处绞刑,监守自盗满四十贯即该问斩,然陛下念及勋戚体面,特赦焦敬死罪,杖责其手下八十了事。”
“焦敬屡次触犯律法,初时多有宽宥,直至其再犯,陛下震怒之下,方施以枷号之刑,已是格外开恩。”
“事后未再深究,更在御驾亲征前,特命其辅佐郕王居守京师,此乃托付社稷之重,足见圣心仍信其能感念天恩。”
“正如魏国公一脉,昔年太宗皇帝先削其爵,后复其位,徐氏子孙又岂敢心生不满?为臣者,自当以魏国公为楷模,至于皇亲贵胄,更当以身作则。”
张祁冷眼旁观,心知于谦这番话确是发自肺腑。
在于谦眼中,君臣大义高于一切,即便受罚,也该感念皇恩。
然而孙太后与明英宗这对母子向来是以己度人,自然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唾面自干,以为天下人都如他们一般睚眦必报。
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倒真是做贼心虚的最好写照。
当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孙太后与明英宗这对母子的猜忌与多疑反倒更合乎人性。
他们深知,所谓“忠君大义”,不过是统治和驯化臣民的话术,这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教化,终究要靠刀剑与枷锁来维系。
如今龙困浅滩,权柄易手,这对尝遍权力滋味的母子,怎会相信那些曾被他们肆意折辱的大臣,真能如于谦这般恪守臣节?
在这对母子眼中,于谦的耿介是罕见的异数,世上多得是伺机报复的“乱臣贼子”。
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于谦的赤胆忠心,是出自纯粹的家国情怀。
当然孙太后不能直接对于谦道出她这种阴暗心理,她的鎏金护甲在紫檀案几上刺啦刺啦得划拉了半晌,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理由,“老身想起一桩旧事,正统十年时,成国公朱勇曾弹劾焦敬、赵荣等一众勋贵懒惰疏慢,不肯奉诏习骑射。”
“这连弓马都不甚娴熟之人,如何统领三千营与神机营这等精锐?莫不是要误了将士们的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