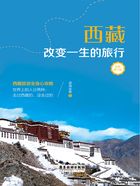
现实世界里的香巴拉或香格里拉
藏传佛教的香巴拉是千余年来信徒们憧憬的人间净土,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背叛。二者除发音相似,本质上并无关联。但取其理想世界的一面,二者却是可以等而论之的。二者也均系人们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世界中无对应之物。
但是,人之本性使然,寻找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藏族人千百年来对香巴拉的苦苦追寻,西方人对香格里拉数十年来的痴心向往,两股潮流最终汇在了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寻找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戏剧,在雪域高原上拉开了序幕。
二战后的几十年内,一些地方陆续宣称在本地找到了“香格里拉”,或者被外界游客认为是“香格里拉”或“最后的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雪山水晶国”拉达克、印度的巴帝斯旦,尼泊尔的莫斯唐、不丹,滇西北的中甸、德钦、丙中洛,川西的稻城,藏东南的墨脱、察隅,巴基斯坦的罕萨山谷,甚至中亚的某些偏僻角落。其中尤以印度的巴帝斯旦、尼泊尔的莫斯唐、滇西北的中甸、川西的稻城影响最大。
2001年,云南率先将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2002年,四川也将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的日瓦乡改名为香格里拉乡。他们像精明的商人,以为给某个地方注册了“香格里拉”的商标,有了合法的依据,从此财源滚滚,大可安枕无忧了。但是,似乎尘埃并没有落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有人认为所谓考证论证,不过是附会、曲解甚至编造而已。比如,中甸之为香格里拉的重要依据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东方奇女”刘曼卿在《康藏轺征续记》中的记述:“讵三日后,忽见广坎无垠,风清月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牛羊成群,帷幕四撑,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恍惚武陵渔父误入桃花源仙境,此何地欤!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也……民性勤俭朴实,不尚虚华,更无非分之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浑浑噩噩,不知世事。”然而这只不过是断章取义的把戏。《康藏轺征续记》里还有这样的叙述:“全城街道共只两条,牛马杂沓,泥泞不堪,积臭令人掩鼻……将谓中甸人民果真长年居于桃源仙境欤?是又不然。”此外当年中甸盗匪横行,仅归化寺(今松赞林寺)内,有枪八九百支,“本自卫之本能,中甸遂亦家家购置枪械”。更不消说什么“卡拉卡尔”即“卡瓦格博”“香巴拉”的当地方言是“香格里拉”等说法。中甸是谓香格里拉欤?是又不然。稻城、德钦等地,与此大致类同。
此外,大多数“香格里拉”们有意无意把至关重要的一点给忽略了。无论是佛教典籍记载或民间传说中的香巴拉,还是希尔顿笔下在“the wilds of Tibet(西藏蛮荒之地)”的香格里拉,都明白无误地表明,香巴拉或香格里拉与荒寒的高原紧密相接。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香巴拉才会被饱受高原严酷寒冷气候折磨的雪域居民视为人间乐土。
想象一下,当从小生长在冬季长达半年以上的酷寒高原,整日面对漫无边际的荒漠和空茫苍凉的冰天雪地的雪域居民,一旦他翻越过喜马拉雅山的一个丫口,只需向前行走二三十千米,就来到了一个四季如春、遍地花开、野果满山、森林密布的热带地区,眼前的景象对他而言,显然已完全超出了理智所能到达的范围。时间在惊慑过度的心灵里留下了一段空白,当渐渐恢复了一部分意识,他的口中喃喃着的,唯有那一个梦幻般的词语:香巴拉!香巴拉!
这样的地方,西藏乃至整个藏区只有一处,它正是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传说是观世音菩萨的一滴眼泪绿度母幻化成的一朵白色莲花——墨脱。
令人遗憾或者该庆幸的是,在市声喧哗人心浮躁的时代里,这一朵美丽的莲花,仍沉静如独在深闺的女子,含羞开放在雪域秘境之中。在西藏人眼里,墨脱是远在南方的神秘净土香巴拉。虔诚的佛教徒把去墨脱朝圣一次视为终生之幸,而一般人则畏于险途,“今生只能向往了”!
关于香巴拉或香格里拉花落谁家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但心怀“桃花源情结”的人不会理睬别人的判断。他们还将继续寻找下去,直到找到自己的香巴拉或香格里拉,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内心的深处。

去往墨脱路上之嘎隆拉山山顶天池。凶险中藏有最美丽的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