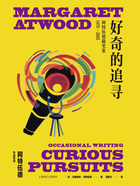
评《安妮·塞克斯顿:信中的自画像》
安妮·塞克斯顿是同代之中最重要的美国诗人之一。批评家对她诗作中强烈的“忏悔式”特征既有赞扬也有指责。起初,很容易就能对她置之不理,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常常不为所动,认为只不过是又一个整天关在家里快被逼疯的神经质家庭主妇想要写作。但要一直对她视而不见并不容易。她确实是个家庭主妇,也确实神经质——她在信中对这两点都非常肯定——但她有能量、才华和理想。尽管直到二十九岁才正式开始写作,但在十八年诗歌生涯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出版了九部作品,收获了诗歌所能给予的所有世俗成就。获得了一座普利策奖,出席了国际诗歌节,还挣得了一份大学教职——尽管她本人从没上过大学,同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一九七四年,在没有直接原因的情况下,她在马萨诸塞州韦斯顿的家中自杀身亡。
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她一直想让这本书信集成书。她任命了一位遗稿保管人和一位传记撰稿人,而且在成年以后不断收集并保留了大量的物品——干花压花、舞伴记录卡、明信片和快照。她还留下了用碳纸复写的信件复本,这本书的编辑们不得不阅读了五万件各类材料,然后才选出了这相对的一小部分。你读完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向焚化炉,不是要烧掉这本书,而是烧掉自己留下的垃圾堆。我们之中真的有人,愿意在自己死后,让陌生人读我们写给高中男朋友的肉麻求爱信、琐碎的流言蜚语和私密的情书吗?出于某种与她最后的自杀行为或许并非无关的原因,安妮·塞克斯顿这样做了。她小心保存的往来书信,是她花去大半生时间为已故的自己修筑的纪念碑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停住时间,并把自己也关在里面,那未来不管什么不知名的怪物就都没法抓住你了。而安妮·塞克斯顿对于未来有着深深的恐惧。
诗人写的信并不一定比银行经理的信有趣多少,但安妮·塞克斯顿是一位非凡的书信作者。虽然,正如她的编辑们煞费苦心所表明的一样,她常常难以接近,有时几乎无法共处,但她把最好的自己留在了通过书信建立的交往之中。她很可能觉得,有了书信的距离,与人打交道会更容易。无论如何,她所执笔的信——即便是写给据说她不喜欢的人——也充满魅力,富有创意,亲密而有活力,虽然有时太过急于取悦,甚至趋迎奉承。当然,其中许多信件是写给其他作家的,其间满是文学掌故,以及让历史学家欢欣不已的细枝末节,但抓住读者注意力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那委婉曲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书信表达本身。
然而这并不是安妮·塞克斯顿的声音;这只是她的一种声音。她本人也一直习惯于将自己一分为二——“好安妮”和“坏安妮”——信是“好安妮”写的。一个更加忧郁的声音写就了她的诗歌,还有另一个声音则负责她一生之中标志性的盛怒、妄想发作、精神崩溃、不知羞耻地玩弄他人和酗酒。她对朋友非常苛刻,永不知足地渴求关注,尤其是认可和关爱。她是恣意张扬的浪漫主义者,几乎能够在同一分钟里同时经历极端的愉悦和极度的忧郁。但我们是通过她意志坚强的编辑们——其中一位是她的女儿——了解到她的这一面的,道貌岸然维持体面的诱惑无疑是强烈的,但他们克制住了,这一点值得称赞。在他们手中,塞克斯顿的形象既非女英雄也非受害者,而是一个棱角分明、复杂多面,时常充满爱意,时而又叫人难以忍受的人。
但这些书信本身并不完全是一张“自画像”。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书信一样,塞克斯顿的信读起来像是一种遮掩,一副无忧无虑的面具。普拉斯那令人窒息且常常语气呆滞的书信体,和那个写下她卓越诗句的人几乎没有一点关系。塞克斯顿的信件和诗歌更加接近,但两者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即便是在描写她本人的自杀尝试时,塞克斯顿的信件读起来也不像是出自一个想要赴死之人的手笔,反而非常像是一个热情地渴望活着,也渴望热情地活着的人。
对她而言,这份渴望和她最终的自杀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尽管她曾经说过,自杀是诗歌的对立面,但她也同样能够将自杀推想为一种手段,用来获得“某种力量……我猜我把它看作是逃脱死亡的一种方式”。(不出所料,她很快又回到现实,接着写道,“不管我对它有再多有趣的设想,自杀也只不过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法。”)
自杀既是对于活着的人发出的谴责,也是挑战他们的一道难题。正如诗歌一样,自杀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且拒绝回答对其终极原因的质问。这一行为的不幸后果是让作者的生命变得模糊不清,唯独留下死亡之谜。
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安妮·塞克斯顿身上将是一种遗憾。这些信件应该被人阅读,不仅是为了其中必然包含的有关她自杀的线索,更是为了它们的勃勃生机和坚定信念:并非为了死,而是为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