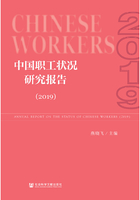
三 职工就业质量情况
高质量就业是职工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就业质量包括劳动报酬、培训和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涉及一系列的指标,由于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和职业卫生等内容,有专题报告进行分析,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重点关注工资收入、就业身份、工作时间和就业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情况。
(一)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不同群体工资差距扩大
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和农民工名义工资增长速度比2017年度均有所上升,均高于同期GDP增速。
近年来,不同类型职工群体工资差距明显,部分群体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职工群体的工资水平,2009年以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55倍,到2018年扩大到1.66倍;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农民工收入从2014年的1.64倍扩大到2018年的1.85倍(见图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与农民工收入总体上差距不大,但也呈现出差距扩大的态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职工的工资差距也较为明显。

图8 2009~2018年不同职工群体年平均工资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雇员比例有所上升,灵活就业规模巨大
2017年,在全国就业人员身份构成中,雇员占56.9%,雇主占2.8%,自营劳动者占37.4%,家庭帮工占3.0%。在城镇就业人员中,雇员占73.1%,雇主占3.9%,自营劳动者占20.2%,家庭帮工占2.8%。目前,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有9766.26万人为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就业身份也称为就业地位,反映了劳动者经济风险的程度以及个人与工作岗位之间的联系程度。雇员的风险比较低,就业岗位较为稳定,可以受到相关劳动法律的保护;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则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属于灵活就业。[5]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雇员的比例会逐渐提高。从数据来看,我国近年就业身份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趋势。这些变化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以及农村中农业产业化、土地流转后企业经营增多等因素有关。
从自营劳动者的特征来看,在就业人口中学历水平越低成为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可能性越大,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占全国自营劳动者的比例达到86.1%。可见,大部分自营劳动者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专业职业技能,因此其就业质量通常较低。
从自营劳动者的年龄来看,除去16~19岁年龄段外,随着年龄增长,成为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与人随着年龄增长,缺乏技能并且学习能力减弱有关,他们只能游离于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打零工等自谋生路的自营劳动者。
从自营劳动者的性别来看,女性的比例比男性稍高,但差别不大。2017年,在男性中只有21.1%的比例为自营劳动者,1.2%为家庭帮工;在女性中有18.9%的比例为自营劳动者,5%为家庭帮工。自2012年以来,其他各年份的情况与此类似,均是女性在自营劳动者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
在灵活就业人员中,除了大量的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外,还有大量的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等人员。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出现了一大批介于雇佣劳动者和自营劳动者之间的新兴就业形式。这种有别于传统就业的灵活就业形式,由于雇主规避责任以及劳动法律法规滞后于现实发展,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就业稳定性等方面都缺乏保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但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带来了挑战。
(三)过半职工存在加班现象,部分企业实施“996”工作制
2012~2017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2013年和2014年达到峰值46.6小时,2015年陡然下降至45.5小时,2016年和2017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2017年回升到46.2小时,从2018年部分月度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比2017年略有下降或基本持平,2019年不同月份工作时间波动较大(见图9)。

图9 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从就业质量角度来看,员工工作时间不足和大量加班都是就业质量低下的表现,工作时间不足属于非充分就业,超时加班则会影响劳动者的休息和健康,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表现。从城镇就业人员工作时间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周工作时间不足40小时的就业人员比例有所下降;处于标准工时40小时的就业人员比例有所上升;加班情况虽然比2014年有较大好转,但加班现象仍较为突出,2017年有50.3%的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1小时及以上,有31.2%的就业人员在48小时及以上(见表1)。
表1 2012~2017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布情况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这两种情况会大量并存:一方面由于企业订单不足,减少加班,工作时间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会停止招聘甚至裁员,而要求在职员工加班,以度过困境。2019年,一些互联网企业提出了“996”工作制,即工作时间为早上9点至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与此同时,部分互联网企业进行裁员或停止招聘,或调低工资增长。有相关报道,网易、滴滴等互联网平台均有裁员计划。[6]就业质量下降,引起部分互联网企业职工抵制,提出“996、ICU”的口号,即工作996、生病ICU。“996”工作制一天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再考虑上下班的交通通勤时间,则个人生理活动时间和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将十分有限。这种工作制度无疑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强度的工作必然影响职工的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显然,“996”工作制是与《劳动法》相违背的,企业单方面修改劳动时间,侵犯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北京等大城市的工作时间相对更长,职工工作压力更大。《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就业工作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每天时间为7小时41分钟,居民与就业工作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每天时间为66分钟。[7]从北京就业的人群来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34分钟;交通时间为1小时29分钟,与10年前相比,北京“上班族”工作时间增加近一小时,2008年北京“上班族”日平均工作时长为7小时38分钟。[8]可见,在北京等大城市,职工工作生活不平衡的情况更为普遍和突出。
(四)学历水平持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
技能、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是职工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就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持续提升,2015~201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学历就业人员比例有所下降,高中、中职和职高学历的比例在上升,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7.47%提升到18.23%。
职业教育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初中及以下文化学历的就业人员超过六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是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关键。然而,自2000年以来,职业院校毕业生总体上呈现略微下降,然后上升,再下降发展的态势。与高校扩招及毕业生人数不断增长相比,职业教育发展则略显式微,在生源和师资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与职业教育相比,社会人员培训的发展相对较好,2000年以来社会人员培训数量持续上升,到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则呈现一定的下降。与此同时,很多企业由于担心员工流动等原因,对职工重使用,轻培养,对职工在职培训不愿投入。但是,随着《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相信未来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将会有较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