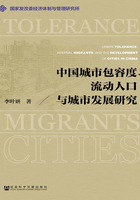
第二节 城市包容度相关研究综述
根据系统论和逻辑学理论,事物的概念包括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和特性,外延是指概念或定义所指事物的范畴或数目。本书对城市包容度的研究述评也不例外地分为这两个方面,以求更深刻理解本研究的核心要素与研究体系。
一 城市包容度的内涵与外延
包容(tolerance)起源于16世纪西方教派分裂、宗教矛盾激化历史语境下对不同信仰的包容,通常称为宗教宽容。英国、奥地利等国都曾专门颁布《宽容法案(法令)》。当今社会的包容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了极大的扩展。2016年3月1~3日,世界银行召开了“2016年脆弱性论坛”(World Bank Group Fragility, Conflict and Violence Forum 2016),其主题正是“行动起来构建和平与包容性社会”(Take Action for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关于城市包容度的定义,Richard Florida曾提出它代表了对各少数民族、各种族和各行各业群体的开放性、宽容性和多样性,但后续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J]. Washington Monthly,2002,35(5): 593-59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Reese和Sands针对Florida的定义指出,他利用对人口多样性的度量来代表包容度不一定成立,因为没有较好的事实证明多样性和包容度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
Reese和Sands针对Florida的定义指出,他利用对人口多样性的度量来代表包容度不一定成立,因为没有较好的事实证明多样性和包容度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Sands G, Reese L A. Cultivating the Creative Class: And What About Nanaimo? [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2008,22(1): 8-23.](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学者Haifeng Qian进一步对二者间关系做出了实际检验,发现在研究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长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时,包容度应当与多样性区别开来。
,学者Haifeng Qian进一步对二者间关系做出了实际检验,发现在研究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长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时,包容度应当与多样性区别开来。![Haifeng Qian.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J]. Urban Studies,2013,50(13): 2718-273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以上包容度的内涵都是国外学者依据国外实际情况或数据支撑做出的论述或检验。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情存在一定的差距,人口的特征也不尽相同。所以本书对城市包容度的定义更多地采用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根据发展经济学对于贫困的研究,贫困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展,由收入和消费贫困延伸至能力贫困(包括健康、教育、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贫困),后发展到涵盖社会包容性、机会和福利平等性等方面的权利贫困。 这里提到的“权利贫困”正是与本书所讨论的“城市包容度”密切联结的对象。由此引出“城市包容度”的定义:
这里提到的“权利贫困”正是与本书所讨论的“城市包容度”密切联结的对象。由此引出“城市包容度”的定义:
城市包容度是指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内容,评价城市对于流动人口中不同能力(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不同职业、不同出身等类别群体的接纳程度。
在我国,外来人口中比较不受包容、不被接纳的弱势群体大多来源于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群体。笔者的导师刘纯彬教授早在2005年就针对与农民工相关的城市包容度问题做出过详细严谨的论述,只是当时还未曾明确提出“城市包容度的相关概念”。他在实地调查、理论探讨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要着力解决进城民工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养老保障、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民工参加工会等突出问题,改善其生活现状。![刘纯彬.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现状需要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J].红旗文稿,2005(9): 13-15;刘纯彬.农民工需要解决的10个突出问题[J].人口研究,2005, 29(5): 48-5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这正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保障的是城乡劳动力平等进入、平等居住与平等就业的基本权利。
这正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保障的是城乡劳动力平等进入、平等居住与平等就业的基本权利。
如今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将包容的外延扩展至个人价值观、政治意见、文化倾向、种族民族等多个层面。![黄晓敏.中国创意经济的宽容度指数分析[D].天津大学,201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李学迎自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宽容”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历史发展。
李学迎自经济学视角出发研究“宽容”概念和相关理论的历史发展。![李学迎.经济学视野下的宽容[D].山东大学,2009.](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他认为现代宽容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宽容,现代社会宽容包括了古典宽容与现代宽容两部分。本书则将“城市包容度”的外延具体定义为四方面: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包容;社会保障体系的包容;人力资本获得渠道(教育培训资源分配)的包容;市场竞争环境的包容。这也是后文选取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下辖分量的重要参考依据。
他认为现代宽容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宽容,现代社会宽容包括了古典宽容与现代宽容两部分。本书则将“城市包容度”的外延具体定义为四方面: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包容;社会保障体系的包容;人力资本获得渠道(教育培训资源分配)的包容;市场竞争环境的包容。这也是后文选取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下辖分量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 城市包容度理论综述
关于城市包容性的研究近年才兴起,国内研究占少数,国外研究已较丰富。由于国内外研究经济社会背景环境、数据范畴和可得性、对象特征差异很大(异质性较强),因此进行具体分析时需要对国外研究成果加以调整,但国外研究尤其是相关理论创新依然有较高参考价值。目前对于城市包容度指标的选取,学界观点不尽一致,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包括Richard Florida和Haifeng Qian的模型,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Florida包容度理论模型
Richard Florida对包容度的最初论述出现于他在2002年发表于《华盛顿月刊》的文章《创造性群体的跃升》(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及2003年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布鲁金斯评论》(The Brookings Review)收录的文章《技术与包容:多样性对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性》(Technology and Tolerance: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to High-Technology Growth)。![Florida R, Gates G. Technology and Tolerance: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to High Technology Growth[J]. Paper for the Center on Urban & Metropolitan Poli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9(3).](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在Florida的理论体系中,衡量城市包容度(或多样性)的共有四项指数:同性恋指数(Gay Index)、波希米亚指数(Bohemian Index或Boho Index)、外国出生人口指数(Foreign-Born Index)和综合多样性指数(Composite Diversity Index),其中前三项分别为同性恋群体、艺术家或音乐家、出生于美国领土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后一项是前三项的综合排序。他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公共使用微观数据样本中50个大都市的数据对前述四项指数与梅肯技术标杆指数(Milken Tech-Pole Index,代表地区高科技产业集聚和增长,由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于1999年提出)及科技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Devol, Ross C, Perry Wong, John Catapano, Greg Robitshek. America's High-Tech Economy: Growth, Development and Risks for Metropolitan Areas[M]. Milken Institute,1999.](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主要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认为,城市包容度高代表着较低的进入壁垒/门槛,因此较高的城市包容度或多样性能够帮助城市或地区吸引更多的人才(包括高科技劳动力,其中同性恋者、艺术工作者和国际移民是重要标志),他们促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为高科技、高生产率的发展中心。其中与城市科技成功性最显著相关的指数为同性恋指数,因为同性恋群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多样性和革命性的“最后边界”。
主要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认为,城市包容度高代表着较低的进入壁垒/门槛,因此较高的城市包容度或多样性能够帮助城市或地区吸引更多的人才(包括高科技劳动力,其中同性恋者、艺术工作者和国际移民是重要标志),他们促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为高科技、高生产率的发展中心。其中与城市科技成功性最显著相关的指数为同性恋指数,因为同性恋群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多样性和革命性的“最后边界”。
Florida的研究与推广奠定了城市包容度、开放度及社会多样性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包容度等新兴概念引入学者们的视线。此后,城市包容度相关命题开始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较高的城市包容度除可吸引人才、促进城市创新和技术进步外,能够包容艺术从业者、波希米亚人(放浪者或先锋派)和同性恋群体的社区,其房价的提升也受到两方面机制影响:一是艺术设施增强了审美愉悦感,二是开放与包容导致正外部性,这证明了包容度还对房价波动产生较大作用。另外,包容度还通过影响城市整体生产的技能水平间接影响工资收入、就业情况和地区生产总值。![Florida R, Mellander C, Stolarick K.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regional development-human capital,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oler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8,8(5): 615-649; Florida R, Mellander C. There Goes the Metro: How and Why Bohemians, Aartists and Gays Affect Regional Housing Valu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0(2): 167-188.](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二)Haifeng Qian包容度理论模型
来自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Haifeng Qian教授极高地肯定了Richard Florida等学者对城市包容度研究做出的贡献。但他注意到近年来与城市包容度相关的研究多将它与城市开放度、城市多样性混为一谈。因此他将包容度与多样性进一步区分开来,指出它们在定义和测算方法上的差异,及它们推动创新和创业(企业家精神)的不同机制。![Haifeng Qian. Diversity Versus Tolerance: The Soci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J]. Urban Studies,2013,50(13): 2718-273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他认为包容度与多样性定义的主要不同在于:包容度体现了个体指标的重要性,容许更大程度偏离当前个体标准的开放性代表了更高的宽容度;而多样性的增强则体现在对不同社会群体或文化群体均匀分布的改变上。也就是说,包容度更关注于个体的异质性,而多样性更关注于聚类特征和分布。从统计指标上说,较低的相关系数也表明了二者的差异较大。
二者的测算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样性测量借助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设计公式,而包容度测算使用复合的同性恋-波希米亚指数(Gay and Bohemian index)等相关指标。研究所用数据主要为2000年美国大都市统计区数据(US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MSAs),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美国大都市统计区数据(US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MSAs)[EB/OL].美国人口调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metro/.](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最后,在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已有研究比较关注二者对技术、创业、创新、住房和经济指标等方面影响的基础上,Haifeng Qian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根据Romer的新增长理论和Florida的“3T”(Tolerance, Talent, Technology)理论,设计了两个主要的多元分析模型:


其中,包容度变量(tolerance)由同性恋指数(Gay Index,即同性恋者占区域总人口比例)、波希米亚指数(Bohemian Index,即艺术和创造性职业工作者占区域总人口比例)、熔点指数(Melting Pot Index,即国外出生人口或国际移民占区域总人口比例)三者构造而成。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本科学历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表示;集聚度(agglomeration)以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对数值表示;生活质量(amenities)用城市或区域中“NAICS” 排名前五位服务行业的企业数量来表示;university为每千名居民中教职工的比例。
排名前五位服务行业的企业数量来表示;university为每千名居民中教职工的比例。
得出的结论是多样性对创新创业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包容度则是间接的。但二者都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创新创业的开展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
除Haifeng Qian教授外,Karen M. King也在他关于包容度的研究中对Richard Florida的指标体系做出了改进,指出其指标不能良好地反映出地区的经济表现,而且“创造性群体”的界定比较模糊,在衡量城市包容度与区域发展时未考虑不平等与贫困问题。![Karen M. King. Technology, Talent and Tolerance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Canada. Hand Book of Creative Clas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后文也将借鉴前辈们的研究范式,对我国城市包容度的特殊性进行考量,设计并构建我国城市包容度指数体系。
后文也将借鉴前辈们的研究范式,对我国城市包容度的特殊性进行考量,设计并构建我国城市包容度指数体系。
三 城市包容度实证研究述评
实证研究方面,本书主要总结国内学者关于包容度或类包容度指标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包容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视野下的“容忍度”研究,尤其是顾客对旅游产品(包括景区)定价的容忍研究。王霞在她的博士论文中不限于旅游业,对各行业价格容忍度(price tolerance)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分析了顾客满意、价格容忍度和价格弹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她对包容度的定义是“顾客愿意支付或者下次购买时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研究得出行业集中度差异、品牌差异对价格容忍度的影响。该研究跳出新古典价格决定论,考虑了非经济指标对价格弹性和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并且不局限于单行业、单指标。![王霞.顾客满意对价格容忍度的影响研究[D].清华大学,200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黄晓敏曾在就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研究时,设计并构建了创意经济社会宽容度(或社会包容度,social tolerance)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该指数包括4项白色指数和4项灰色指数,包含的具体指标为12项。在总权重为10分的基础上,为每一个指标赋权并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创意经济宽容度的分析。她对社会容忍度的界定为“社会容许不良事件得以存在的最低限度”。![黄晓敏.中国创意经济的宽容度指数分析[D].天津大学,201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这也是国内较详细论述与社会宽容度相关的综合指标的文献之一。
这也是国内较详细论述与社会宽容度相关的综合指标的文献之一。
李学迎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包容度对生产和交易的激励是否节省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以及制度包容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李学迎.经济学视野下的宽容[D].山东大学,2009.](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这与本书的研究较为近似,也与本书在研究城市包容度与产业发展关系时的思路不谋而合。
这与本书的研究较为近似,也与本书在研究城市包容度与产业发展关系时的思路不谋而合。
四 包容性增长相关文献综述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可以体现出对城市包容度水平提升的要求。笔者基于胡锦涛同志的两次讲话内容、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报告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贫困理论、不平等理论发展与增长理论演进中梳理包容性增长理念形成和演变的脉络。
2009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讲话,首次提出主张“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再次以致辞标题的形式强调包容性增长,并充分而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认识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政策建议。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升全球社会的包容性主要是指“全球社会都有责任确保即使是地球上最贫困的人们也不会被遗忘在全球化的浪潮之外”,推进全球化需要正视排斥主义对发展机遇的阻碍。而世界银行发布的另一项《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2014)显示,中国包容性城镇化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住房供给及农村地区服务供给提升来实现。在保证农村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城乡公共服务同质化,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包容性增长的要义。关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外延,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曾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战略主要包括累积型、创新型、分配型、稳定型和就业型五种政策类型。杜志雄、肖卫东、詹琳等也曾论述,“包容性增长”理论上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四个方面;政策上主要指向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使民众获得人力资本价值公平,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使民众获得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使民众获得社会保障价值公平三个层面。![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4-1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这也成为本书界定“城市包容度”外延的重要参考。
这也成为本书界定“城市包容度”外延的重要参考。
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包容性增长、权利平等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贫困源于各方面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变化与包容性增长息息相关。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扶贫减贫密切相关,当我们铲除了权利贫困的源头,才能够让城市在面对从乡镇转移来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时更具包容性(城市包容度更高)。从单纯强调极化涓滴效应的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益贫式增长或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包容性增长,增长理论得到不断改进。![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4-1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笔者研究发现,目前与包容性相关且被提及较多的就是规划、发展和增长,其中以增长频率最高。其实“包容性规划”也是许多美国和欧洲城市当前实行的政策,![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总报告[EB/OL].世界银行网站[2014- 03- 25]. http://www.shihang.org/zh/country/china/publication/urban-china-toward-efficient-inclusive-sustainable-urbanization.](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值得我国政府在规划决策时借鉴。
值得我国政府在规划决策时借鉴。
五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及家庭分别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幸福感指数及居住分离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多,但从城市包容度视角进行研究的尚少。与城市包容度最为相似的研究视角是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对过往相似研究的总结,也将对本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带来极大的启发。
(一)社会融合的内涵和外延
根据张文宏、雷开春![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5): 117-14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毛丹
、毛丹![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9(4): 28-60.](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黄晓燕
、黄晓燕![黄晓燕.新市民社会融入维度及融入方式——以天津市外来人口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0(3): 100-10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张广济
、张广济![张广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3): 42-4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陈成文、孙嘉悦
、陈成文、孙嘉悦![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 66-7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周皓
、周皓![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3):27-37.](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周琳雅
、周琳雅![周琳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叶鹏飞
、叶鹏飞![叶鹏飞.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研究——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的数据分析[J].城市学刊,2015, 36(3): 6-1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等对社会融合概念的定义:流动人口逐步被流入地主流社会关系和文化所接受,实现与当地经济、社会等资源的良性互动及身份变换的过程就是社会融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人口空间流动或迁移问题,更是外来人口在思想观念、社交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向城市居民转型的过程。
等对社会融合概念的定义:流动人口逐步被流入地主流社会关系和文化所接受,实现与当地经济、社会等资源的良性互动及身份变换的过程就是社会融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人口空间流动或迁移问题,更是外来人口在思想观念、社交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向城市居民转型的过程。
关于社会融合的外延,张文宏、雷开春以上海为案例,界定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四方面——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层面的融合程度呈依次递减趋势,即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较高,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较低。杨菊华也定义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即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等。![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 17-29.](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悦中山等人综合前述研究,将四维度重新整合分类为三维度,提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方面。
悦中山等人综合前述研究,将四维度重新整合分类为三维度,提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方面。![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2(1): 1-1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二)社会融合相关理论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社会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早,因此相关模型主要采自国外经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帕克(Park)首先提出种族关系周期理论,![Park Robert Ezra. Race and Culture[M].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0.](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戈登(Gordon)随后发表著名的七阶段同化论,
戈登(Gordon)随后发表著名的七阶段同化论,![Gordon Milt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这开创了社会主流文化单维度融合模型的先河。
这开创了社会主流文化单维度融合模型的先河。
此后逐渐发展出的双维度以及多维度模型理论。双维度模型以Berry社会融合模型![Berry J W.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iandis H C, & Brislin R W(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ocial Psychology(vol.5)[M]. Allyn and Bacon Inc. ,1980.](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为代表,维度I是个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保持本族群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维度II是个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并总结出四种社会融合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和边缘化。多维度模型以鲍里斯(Bourhis)等人的“交互性社会融合模型”为代表,模型剖析了流动人口主观能动性、流入地公共制度与政策、流入地居民态度等三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社会融合问题。
为代表,维度I是个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保持本族群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维度II是个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并总结出四种社会融合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和边缘化。多维度模型以鲍里斯(Bourhis)等人的“交互性社会融合模型”为代表,模型剖析了流动人口主观能动性、流入地公共制度与政策、流入地居民态度等三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社会融合问题。![Bourhis R Y. , Moise L C. , Perreault S, Senecal S.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7,32(6):369-38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三)社会融合实证研究综述
我国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自2011年起至今每年发布一次《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2015[M].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201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3943A8/11064912404461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32723-yVCNu5b5V0tVlFn1VZB9ixLOQSScuRim-0-2baf85412a908c0bd3f669c1a1be7119) ,每次都包含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相关专题,展现出对社会融合问题的极高关注度。这是国内对该专题比较系统、持续的研究,包括对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对指数合成结果的描述性分析及对指标体系内各分量的应用研究。表2.1展示的是社会融合指标的最初设计构架,但该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繁多的指标变量容易掩盖个体异质性,整合后无法分辨子维度或子指标下流动人口的融入难度;把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纳入社会融合指标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会造成运用综合指数和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时出现共线,导致系数估计不稳定、方差增加较快,影响估计或预测的准确度。由于存在局限性,该指标体系发展至今已经被诸多专家学者几经讨论修改。2015年指标详情请见第四章表4.1。
,每次都包含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相关专题,展现出对社会融合问题的极高关注度。这是国内对该专题比较系统、持续的研究,包括对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对指数合成结果的描述性分析及对指标体系内各分量的应用研究。表2.1展示的是社会融合指标的最初设计构架,但该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繁多的指标变量容易掩盖个体异质性,整合后无法分辨子维度或子指标下流动人口的融入难度;把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纳入社会融合指标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会造成运用综合指数和经济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时出现共线,导致系数估计不稳定、方差增加较快,影响估计或预测的准确度。由于存在局限性,该指标体系发展至今已经被诸多专家学者几经讨论修改。2015年指标详情请见第四章表4.1。
表2.1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构成(2010年)

注:作者根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第二章“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相关内容编制。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基于上述指标体系,连续五年对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就业与社保、户籍改革、家庭居住分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专题性研究,得出了对流动人口服务工作有价值有依据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