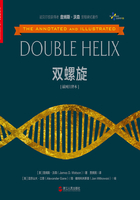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4
初识威尔金斯
莫里斯・威尔金斯并不是出于严肃的科学目的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出发,这次旅行是他的上司兰德尔教授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礼物。兰德尔本已安排好了行程,打算亲自去参加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描述自己新创办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完成的一些研究工作。后来,兰德尔发现自己实在分身乏术,只好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如果一个人都不去,对兰德尔教授所在的国王学院实验室来说并不光彩,因为他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得到了相当可观的资助,而且动用的是稀缺的国库资金。有不少人质疑,这种做法劳民伤财。

兰德尔参加物理系一年一度的板球赛,摄于20世纪50年代

工人们在清理伦敦国王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的弹坑
在意大利召开的这类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发言通常不需要长篇大论。一般而言,这种会议通常会有一些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参会,而意大利本国参与者则很多,会议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是参加会议的意大利人英语通常都不会太好,当有人说英语说得很快时,几乎没人听得懂。每次会议的高潮部分照例是到某个景色秀丽的景区或寺院进行一日游。因此,参加这些会议,除了听别人说一些陈词滥调之外,与会者很少有机会真正受益。

那不勒斯街景,沃森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满大街闲逛和阅读上”
当威尔金斯到达那不勒斯时,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我明显坐立不安,并且急于回到北方(哥本哈根)去。卡尔卡这次算是真的把我引人歧途了。在那不勒斯的前六个星期里,我一直觉得非常冷。官方气象台公布的温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重要的是那里没有集中供暖设备。无论是在动物学研究所还是在我居住的寓所里(一间位于一栋19世纪建筑楼顶的破房间),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那么一丁点儿兴趣,我就会去做实验。因为做实验时可以四处走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候,卡尔卡偶尔会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架势大发宏论,而我则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次我甚至能听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是否能听懂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卡尔卡的头脑中,基因从来未曾占据过主导地位,甚至连边儿也沾不上。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满大街闲逛和阅读早期发表的关于遗传问题的期刊论文上。有时候,我会做些白日梦,想象着自己发现基因奥秘时的情景,但是我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想法。因此,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一事无成,这种忧虑很难排解。尽管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找工作的,但这根本不能使我感到一丝宽慰。
我仍然保留了一线希望:在这个即将召开的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我也许能够获得某种启发。虽然我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肯定会比期刊论文更加容易理解(那些文章我总是读过就忘)。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兰德尔将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时,讨论核酸分子三维构型可能性的论文还几乎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可否认,这个事实对我在学习化学知识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既然连化学家们自己也讲不透核酸的结构,我又何苦强打精神去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
当然,这也是时势使然,当时确实还无法真正揭开核酸结构的奥秘。 那时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其谈。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大部分论据仍然软弱无力。很多人信心百倍地提出了诸多想法,但它们看上去都是异想天开的结晶学家们的“杰作”,这些人喜欢在一个自己的想法很难被他人证伪的领域里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包括卡尔卡在内的所有与会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X射线工作者的思想,但也没有人感到不自在。这也使得为了迎合这些荒谬的想法而去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的导师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设想过这种可能: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竟然会与一位X射线结晶学家一起进行研究。
那时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其谈。尽管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大部分论据仍然软弱无力。很多人信心百倍地提出了诸多想法,但它们看上去都是异想天开的结晶学家们的“杰作”,这些人喜欢在一个自己的想法很难被他人证伪的领域里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包括卡尔卡在内的所有与会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X射线工作者的思想,但也没有人感到不自在。这也使得为了迎合这些荒谬的想法而去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的导师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设想过这种可能: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竟然会与一位X射线结晶学家一起进行研究。
无论如何,威尔金斯没有令我失望。他是兰德尔的替身也好,他报告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好,对我而言都一样。反正在此之前,他们两个人我都不了解。威尔金斯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与其他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人的发言当中,有几个与这次会议的目的毫不相干)。幸运的是,那些发言都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来自国外的与会者溢于言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太失礼。其中有几个发言人是动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他们都是欧洲大陆的生物学家,这几个人的发言都只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对比之下,威尔金斯报告的DNA X射线衍射图则恰好切中会议主题。这张衍射图是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才被放映在屏幕上的。威尔金斯说,这张图给出的细节比前面几张图更多,他还说,事实上已经可以认定这张图源于一种结晶物质。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但是他干巴巴的英语却使他无法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一旦搞清楚了DNA的结构,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基因的作用机理了。

威尔金斯和戈斯林拍摄的DNA X射线衍射图,在那不勒斯会议上,威尔金斯给与会者展示的正是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

戈斯林将DNA链缠绕在一只折弯了的回形针上,他在拍摄如上图所示的那张照片时,使用的是伦敦国王学院化学系的RayMax密封型X射线管

威尔金斯用来拍摄X射线衍射照片的X射线管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听到威尔金斯的演讲以前,我一直在担心:基因的结构可能是极度不规则的。现在,我终于知道基因能够结晶,既然如此,它一定具有规则结构,这种结构只需要用某种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测定。于是我立即开始设想与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的可能性。我想在他讲演结束后找他聊聊,也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讲演的内容还要更多些。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科学家不是绝对肯定自己是正确的,就不会公开自己的发现。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斯交谈,讲演一结束他就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会议主办方组织所有与会者到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古希腊神庙去游览,我才获得了结识威尔金斯的机会。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和威尔金斯搭上了话,并且告诉他我对DNA非常感兴趣。但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出什么,我们就不得不上车了。我只好陪着刚从美国到这里的妹妹伊丽莎白游览。在神庙里,所有人都散开了。在我再次找到机会与威尔金斯说话以前,我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显然已经注意到我妹妹了,因为她非常漂亮。吃午餐时,他们坐在了一起。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一个又一个傻瓜追求着。现在,改变她生活方式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也许,我不必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家伙了。而且,如果威尔金斯真的爱上了我的妹妹,那么,我也就有机会与他利用X射线衍射对DNA结构展开合作研究了。

帕埃斯图姆有三座古希腊神庙,均建于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460年之间,其中有两座献给女神赫拉,另一座献给女神雅典娜

伊丽莎白·沃森,当时她正乘船横渡大西洋,摄于1951年
当时,看到我走上前去之后,威尔金斯说了声抱歉就独自走开坐到了一旁,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显然威尔金斯是一个很懂礼节的人,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威尔金斯合作的美梦就化为了泡影。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回旅馆去了。无论是我妹妹的美貌,又或是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没有使他“落入圈套”。看来,我和他未来在伦敦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此,我动身回到了哥本哈根,并且不再多想我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前景。

卡尔卡在哥本哈根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前排从左路到右依次为:赫尔曼·卡尔卡、奥德利·雅囡(Audrey Jarnum)、雅特·海泽尔(Jytte Heisel)、尤金·戈德瓦瑟(Eugene Goldwasser)、沃尔特·麦克纳特(Walter McNutt)和E.霍夫-约根森(E.Hoff-Jorgensen);后排:冈瑟·斯腾特、尼尔斯·奥利·克耶尔加德(Niels Ole Kjeldgaard)、汉斯·克列诺(Hans Klenow)、詹姆斯·沃森和温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